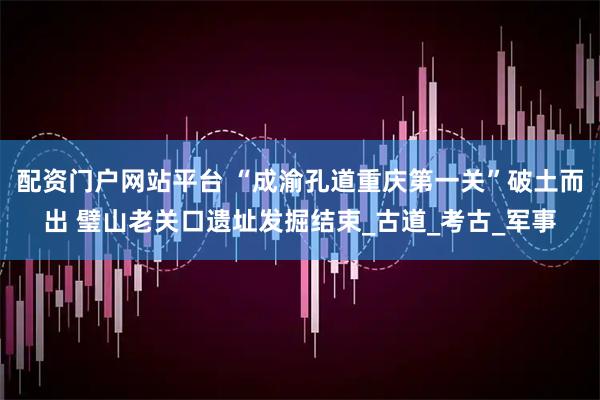
青灰色的条石重见天日配资门户网站平台,沉寂数百年的关隘轮廓在缙云山脉的拖木槽垭口逐渐清晰。近日,素有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之称的老关口遗址考古发掘顺利收官。
8月12日,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、老关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黄伟向记者介绍,作为重庆区域内成渝古道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,此次成果不仅揭开了老关口作为重要军事关隘的完整形制,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当下,为这条千年动脉注入了可触摸的历史厚度。
系统发掘还原雄关原貌
这座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是如何浮出水面的,随着黄伟的讲述,谜底被渐渐揭开。
黄伟说,此次考古发掘采用了“口述史收集+田野踏查+勘探解剖+系统发掘”的综合技术路线,考古人员在缙云山脉“两山夹一槽”的独特地貌中勾勒出雄关旧影。
老关口遗址地处缙云山脉龙隐山拖木槽垭口,位于璧山区、江津区、重庆高新区交界地带,是缙云山脉重要垭口通道,也是连接成渝古道东大路白市驿、来凤驿的制高点,在防御和交通往来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展开剩余76%老关口遗址。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根据考古成果推测,明朝时期老关口还仅是成渝两城往来通行的重要道路。直到清代中后期,因为老关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特殊地理位置,古道上才开始修建关隘。当时的人们通过开凿道路两旁山体,将垭口拓宽,并因地制宜地用开凿的土石将老关口古道的地势垫高了两米多。随后,便在这片人工填起的平台上重铺了道路,建起了关城,使其成为成渝古道上拱卫重庆城的一个重要关口。
那么重新铺的老关口成渝古道有多宽呢?
黄伟给出了答案:超过3米,大致3.1-3.5米不等,符合当时官方规制,可以并行两匹骡马。
目前,考古队员们已初步厘清遗址的结构布局,在遗址东侧发现“古老关口”城门及第二道城门,南北两侧设有营房、哨楼等军事设施,西侧则分布着大城门、小城门及相连的城墙。遗址内除军事设施外,还揭露了石板道、石碥道等道路系统,以及排水沟、水缸、便池等生活设施,印证了其作为行政边界与军事险隘的双重地位。
老关口遗址营房介绍。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沧桑古道见证川渝交通变迁
老关口为什么会被称为“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”呢?
老关口遗址鸟瞰。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璧山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,老关口扼守的东大路,自明初便载入国家驿传体系。洪武二十七年《寰宇通衢》清晰标注了“朝天驿六十里至白市驿,六十里至来凤驿”的脉络。作为“五驿、四镇、三街子、七十二场”中声名显赫的驿站之一,来凤驿在明清两代肩负传递公文、迎送官员的重任,其管辖虽在巴县、永川、璧山间几度流转,但始终是东大路的心脏节点。
这条古道更是军事博弈的血脉通道。明代急递铺铺兵以昼夜三百里的速度接力传递文书;清代绿营汛兵沿路设塘,自重庆浮图关起,头塘、二塘依次西延,老关口所在的拖木槽塘(七塘)至界牌铺塘(十二塘)六塘相连,构成严密的军事通讯网。
明天启年间石柱女将秦良玉驰援平叛、清初吴三桂大军压境入重庆、清咸丰年间张五麻子围困璧山……金戈铁马一次次碾过东大路的石板,老关口“险设天成”的石刻题记,正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无声诠释。
当硝烟散尽,商旅足迹让古道重现生机。晚清至民国,东大路每日滑竿商贾穿梭两三千人,驮运牲畜往来二百余头,成年累月的重压甚至在石板路上刻下数厘米深的印槽。这条官道早已超越军事交通意义,成为川渝之间文化交汇的血脉纽带,催生了如道光二十八年巴县知县朱凤枟题刻“巴县西界”与“险设天成”等众多遗存,诗人学者往来酬唱的翰墨风流亦在此沉淀。
遗址保护衔接古今记忆
随着20世纪30年代成渝公路贯通,马蹄声与车轮声渐行渐远,老关口的军事光环悄然黯淡,深埋于时光尘土之下。直至此次系统发掘,这座成渝走廊上的地理坐标与文化符号才重新“破土”。
璧山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,璧山区后续将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携手,推动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。让关隘城墙、深深车辙这些凝固的史诗,从文献记载走向具象呈现,使公众得以亲手触摸成渝古道共同的历史脉动。
当旧时戍卒的目光与今人相遇,一段被古道串联的双城记忆将在保护与传承中重获新生——这不仅为区域文旅融合注入灵魂,更在巴蜀千载同风的画卷上,增添了厚重而鲜活的一笔。
丛林中的老关口遗址。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
老关口遗址的苏醒,恰似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宏大叙事中嵌入一枚历史榫卯。它无声讲述着两地山水相依、文脉同频的千年过往,也为走向更深融合的未来,奠定下一块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。
原标题:成渝孔道第一关破土而出 璧山老关口遗址发掘结束配资门户网站平台
发布于:重庆市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